不知从何开始,人们好谈“经验”,特别是在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在对“经验”的推崇中,“生存经验”“生活经验”或所处的生活境域、日用常行或日常的生活世界,被提到了至上的地位。按其内涵,这种被注重的经验,虽然常常被视为生活过程的内容,但实质上又总是与所谓术数相关,也就是说,以上视域中的“经验”既和早先的生活过程相联系,也关乎沟通人的存在与超验世界的巫术,其中有非理性的方面。然而,对以“经验”为指向的进路来说,从价值系统到形上之知,都无不本于所谓生活“经验”:“‘经验’是哲学更‘原初’的对象和‘根本出发点’”;“深入诠释古典生活经验,不仅应该是中国哲学史书写的重要工作,更是激发中国哲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同样,近代以来的“语汇体系和语义结构”,也被视为以“经验的展开为前提”,对语言衍化的考察,内容不外乎研究“作为一种特殊经验形式的言语实践如何推动语言在经验之流中的嬗变和绵延”(《哲学动态》,2024年第10期)。事实上,经验内在地呈现个体性的品格,张申府已指出了这一点:感觉、经验、实践,都“是私的”(《思与文》)。詹姆士也从宗教经验的考察中,形成了类似的看法,认为宗教意识的神秘性与“私人的宗教经验”相关(《宗教经验之种种》)。经验的这种个体性(所谓“私”)使之无法为理解世界提供全部的源泉。与个体的经验相对,语言则具有公共性,张申府的如下看法,也肯定了这一点:“言语文字是公共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思与文》)而语言所具有的这种社会性或公共性,显然使之难以仅仅来自“生活经验”。
从理论的层面看,经验属于认识论范畴,与概念性认识相对而言。在推重经验的同时,人们往往表现出贬抑理性概念的趋向:按照以上思路,经验具有直观性、切近性和前概念等特点,与人的日常存在紧密相关;与之相对,概念则似乎疏离于人的生活,表现为既定、凝固的规范系统。这种分野又常常与中西之辨相关:中国文化似乎一开始便源于重“经验”,西方思想则侧重于概念性思维。这种看法存在很大问题。首先,从历史事实看,中国文化尽管没有现代形式的经验与理性概念之分,但其内容不仅与日常生活相关,而且包含性与天道的形上关切,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之源归结为单纯的“经验”,意味着将其等同于文化人类学视域中的“原始”“特殊”的系统;其次,经验本身并不限于感性知觉,经验与概念的区分也具有相对性,现代的匹茨堡学派已注意到经验与概念之间的联系,其代表人物之一麦克道威尔在《心与世界》(Mind and World)中即明确指出:“经验已包含概念内容”(experience already have conceptual content)。将经验无限拔高,以此超越(乃至否定)理性概念,与现代哲学的以上视域似乎不相容。
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则可注意到,中国文化的衍化过程并非仅仅以所谓“生存经验”或日常的原始体验为关注之点。《易传》已区分“先天”与后天,并肯定“先天而天弗违”与“后天而奉天时”的统一(《乾·文言》)。所谓“先天而天弗违”的内在涵义,即肯定,以制约经验活动的普遍认识形式乃是先于特定经验:通过对现实的认识以把握普遍之道(揭示现实之道),构成了作用于人的特定活动的前提。换言之,在某种认识与实践展开之前,人们已通过历史的过程,形成(获得了)制约这种活动的普遍认识形式,从而,相关规范具有先验(先于该经验活动)的特点,这种先验的形式意义又制约相关的活动(所谓“天弗违”)。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的认识活动又具有“后天而奉天时”的性质:如前所言,规范本身来自人以往的知与行,从而归根到底是基于现实而规范现实,用金岳霖和冯契的观点表述,即得之现实而还治现实。以上看法既不同于后来康德仅仅注重先天性,否定普遍形式的后天来源,也有别于单纯将直接的“生存经验”作为优先关注的存在形态、忽视其中包含先于当下或直接的普遍内容的取向。这一事实同时表明,中国文化固然注重“经验”,但性与天道等形而上是问题一开始便进入其论域。如果着眼于中西文化的衍化,则可看到,西方文化诚然关注逻辑和理性,然而,在苏格拉底之前和苏格拉底之后,生活经验也已成为其关切之点。
进一步考察,关于经验,需要区分科学领域(包含理性概念)与日常经验直观。思想史研究中以经验说事,常常主要关注于日常的经验直观。事实上。与其他观念一样,经验也有具体、现实形态和抽象、片面形态的区分。以其现实形态为关注之点,则可看到,日常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概念更多地纠缠在一起。当人们以经验说事之时,则往往将经验从现实中加以抽取,使之成为片面的形态,以此满足从经验出发的研究偏好。历史上,推重概念、精神的哲学进路(柏拉图、黑格尔是其代表)固然表现出脱离具体和现实存在的趋向,以经验说事,同样也呈现疏离具体现实的问题。如所周知,实证主义者孔徳曾区分了人类思想的不同阶段,包括神学,形而上学、科学(实证),在他看来,在神学阶段之后,人们逐渐追求普遍概念,以此来解释一切现象。在以经验说事的路向中,经验似乎取代了神学,与之相应的是经验的形而上学成为至上的形态。从经验到哲学(形而上学、语言哲学)的这一衍化过程,与孔德所说的从神学到形而上学的进展,给人以异曲同工之感。
从现实形态看,经验内容的把握,离不开概念:在众多的经验现象中辨识某种对象,需要概念的切入,否则可能陷于混沌。辨物析理,都需要概念。按其本来性质,经验具有分离性的特点。蒯因曾指出了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其内容都与经验的分别和对峙相关。首先是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其次是证实原则或还原论,即把所谓有意义的命题或陈述与无意义的命题与陈述分别开来,强调每个有意义的陈述都可还原为直接经验(《经验论的两个教条》)。戴维森则进一步指出,经验论还包含第三教条:即概念形式(conceptscheme)与概念内容(content)的两分(Inquiresinto truth and interpretations)。如果说,分析命题、直接经验、概念形式趋向于抽象性,那么,综合命题、概念内容更多地呈现具体性,经验主义的总体特点在于将二者分离开来甚至对峙起来。与之不同,马克思则注重抽象与具体的结合,形成从感性的具体、到理性的抽象,又从理性的抽象回归具体现实的研究方法。这一进路既展示了把握真实存在的现实取向,也对经验论作了实质的超越。以此为前提,显然难以将思想史的考察,都纳入所谓“经验”之域。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杨国荣︱以经验说事:思想史研究中一种需要反思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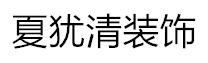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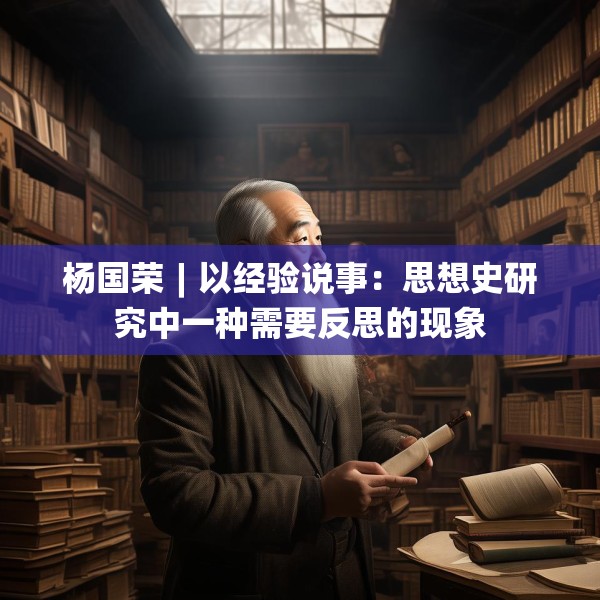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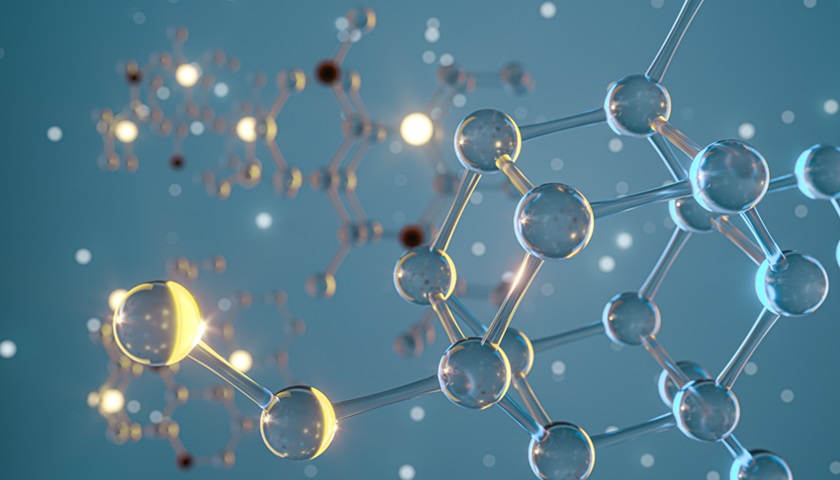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9
京ICP备2025104030号-9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